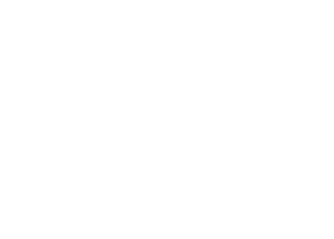在香港,賽馬往往被簡化成一件事:下注、輸贏、刺激;桌遊也常被分成兩類:一類靠氣氛帶動,另一類規則多、門檻高。符國政做的卻是第三種選擇:他把賽馬那種節奏與張力放進桌遊,保留期待與投入感,同時抽走賭博帶來的損失;他又把原本很難共存的記憶元素與派對互動拼在一起,令新手易入門、熟手亦玩得出判斷與策略。他的設計過程,由等待時機、反覆試玩到多次推翻重做,拆解一款本土題材作品如何在「好玩」以外,仍能把價值與文化感放進機制之中,讓更多人願意打開盒、坐低玩,甚至把它變成家庭聚會和教學活動的共同語言。

先等到合適時機,才正式動工
符國政一直想做一個以生肖為主軸的系列作品,構想是每年對應一個生肖,逐步累積成一套完整系列。這個念頭其實早在龍年、鼠年、蛇年都曾出現,相關文件也寫過,但他始終沒有把計劃推到製作階段。他之所以遲遲未動工,並非缺乏熱情,而是對製作風險相當敏感。他習慣把畫師檔期、工廠排期與市場氛圍等因素一併納入盤算,只要關鍵條件未到位,就寧願先按兵不動。直到今年他才判斷時機成熟,於去年七月正式啟動製作,把計劃落實成可上市的產品。


起點其實很單純:想做一款帶記憶元素的派對賽馬遊戲
最初的方向很清晰,他想做一款以記憶為核心的遊戲,讓玩家透過記住資訊,在揭示結果時得到驚喜與刺激。賽馬的「順序」與「變化」本來就適合承載這種張力,因此他以賽馬作主題來承托記憶機制。早期找玩家試玩後,整體反應不差,他一度以為路線已經確立。
但深入下去他很快察覺,記憶遊戲與派對遊戲雖然都容易入門,卻天然存在節奏衝突。派對遊戲講求熱鬧與互動,記憶遊戲則需要相對專注與安靜。要玩家在起哄與互動之中仍能完成記憶判斷,設計難度遠比想像高。也正因如此,市場上同時兼具兩者優點的作品並不多,並非沒有人嘗試,而是融合成本很高。
他坦言過程中也曾想過是否應該放棄或改題材,但最終仍選擇把原本的目標做到底,透過反覆調整規則與節奏,去化解那個看似矛盾的組合。

四次大改、十三個版本
整個製作期中,遊戲經歷了四次大幅度重構,並累積到十三個版本。所謂大改,不是改一、兩個細則,而是核心玩法與體驗都會被推翻重來,以至於第一版與第二版在本質上已經像兩個不同遊戲。這種變化也反映在試玩者的經驗上。有一些長期協助測試的玩家,到最後看到接近完成的樣板再玩時,甚至需要重新確認自己當初玩過的是第幾個版本;有人停在第六版,有人停在第九版,因為每個版本差異都非常明顯。
符國政把這些反覆視為必要的「成本」。他並不追求一步到位,而是透過大量試玩去確保遊戲能達到一個穩定標準:即使玩家類型不同,仍能在多數情況下感受到樂趣。到第九、第十版起,遊戲其實已具備商品化水準,一般玩家會覺得有趣;資深玩家仍可能看得出可再打磨的空間。只是他並不滿足於「能賣」或「能玩」,而是希望它能承擔更清晰的目的。

他想做的不是只給桌遊圈,而是一條能把人帶入門的橋
他希望這款作品能讓平常不玩桌遊的人也願意坐下來嘗試,同時也讓玩開桌遊的人願意拿它作為帶新手入坑的工具。過去很多人都是由派對類遊戲開始,再自然走向更深度的策略作品;但近年玩家群像似乎更分裂,派對玩家繼續玩派對,策略玩家越玩越硬核,兩者之間的流動變少。
他把這款作品定位在一個兩邊都能接受的交界:保留一些易上手、帶節奏的互動感,讓新手不會覺得被規則壓垮;同時又提供足夠判斷空間,令有經驗的玩家不會覺得只有運氣與喧鬧。對他而言,這不只是「做一盒遊戲」,而是在修補一條曾經存在、如今變薄了的入門路徑。

選用賽馬文化做主題,但刻意避開賭博核心
遊戲的另一個明確目標,是談賽馬文化,但不把賭博當作核心驅動。機制上,玩家會把多匹馬放進賽道、安排位置與互相影響,希望自己的馬得到更好的結果;得分方式亦不只是看一、二、三名,而是以不同規則去計算大分與小分,讓比賽過程更有變化。此外,玩家亦可以選擇支持其他人的馬匹,即使自己的馬未必能跑出,也能透過支持策略在對方得分時獲得回報。這種設計保留了「估邊隻會贏」的投入感與討論感,但不引入金錢輸贏與失去資源的壓力。玩家在遊戲中只會累積分數,而不會因為一次選錯而產生強烈挫敗或懲罰感。他用測試觀察來驗證這個方向:真正帶賭博心理的遊戲,輸了的人常會出現明顯情緒反應,甚至小朋友也可能因「輸咗」而不甘或不開心;但在他的測試中,最小七歲的小朋友也沒有出現類似反應。這讓他更確信,遊戲成功呈現了賽馬的張力與期待,但避免了賭博情緒帶來的影響。

賽馬作為香港的集體記憶,可以用更健康的方法去談
符國政並不否定賽馬的吸引力。對他而言,入馬場看賽事、看大屏幕、食熱狗、跟朋友聚會,本身就是一種社交與城市記憶的場景。就算有人小額下注,也未必是為了賺輸贏,而是把它當作活動的一部分。他更在意的是,社會常把「好玩」與「價值」切割:要不只談正面訊息,容易變得說教;要不只追求刺激,卻可能帶來不健康的心理回路。他相信作品可以同時做到好玩與溫和,讓人投入但不需要靠失控或懲罰來支撐樂趣。

因此他把作品放在一個更容易對話的位置:年輕人會想玩、家庭玩得到,同時也能讓人理解「談賽馬不等於鼓勵賭博」。他亦留意到教育機構或會對題材有所顧慮,但只要清楚解釋機制與設計目的,理解是可以被建立的;而且已有老師嘗試把遊戲帶進活動場景使用。



大量試玩後,遊戲反而變得更本土
製作期間,他安排了大量測試:在製作期接觸超過一百位玩家,接近完成後亦再密集測試近一百天。過程中出現一個有趣轉變:一開始遊戲未必那麼強烈「像賽馬」,但隨着玩家回饋累積,大家反而更希望它更貼近香港——包括更本土的馬名、更貼近馬場體驗的氛圍細節。

他亦收到玩家私訊詢問今年維園年宵是否已開始擺攤。有玩家住得很遠,仍表示如果不是因為賽馬主題,本來不會特意走來購買。這些反應令他確認,本土題材的吸引力並非只存在於創作者想像,而是確實能喚起城市共同記憶與身份感。

做得精緻、值得收藏
他最後提到自己對成品感的要求:不只是把規則做順、把平衡調好,也希望作品在體積、用料與視覺上都有完成度,做到細盒而精巧,讓人覺得值得收藏、值得擁有。
這份堅持也總結了他的創作態度:桌遊不一定只是消耗式娛樂,它可以是一種承載記憶、價值與連結的媒介。當一款作品能讓人玩得開心,也能把一段本土文化用更健康的方式說出來,它就不只是一局遊戲,而是能留在生活裡的一個入口。